今天下午全体会议的第四场,将此温哥华年会带向了高潮迭起的情感体验。

加拿大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后代,Joseph,讲述他和他的家族所经历的殖民寄宿学校的创伤故事和历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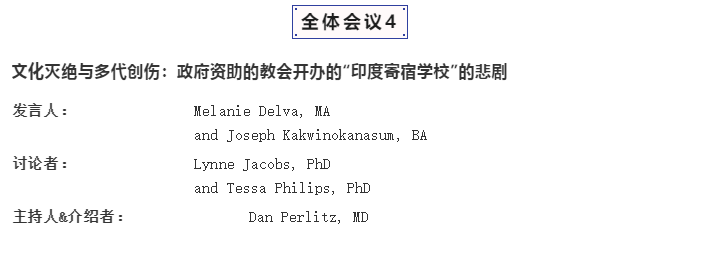
他的祖父母从一出生,就被送到美洲殖民者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;婴儿一出生,就被他们从父母身边抢走,在寄宿学校,学习英语和白人文化;其目的是灭绝印第安语言和文化历史。
当这些孩子长到18岁时,被送回到他们自己的社群;但不幸的是很多人早已经在进入寄宿学校时,夭折了。寄宿学校的条件很差,充满了种族歧视和文化敌视的氛围,很多幼儿被折磨,殴打,甚至强奸。勉强活下来的人,当他们被“释放”时,也已经负载了严重的心理创伤。
他们吸毒,滥交,自残,生活得空虚与无意义;更加残忍的是他们的下一代,也就是Joseph的父母,又被再一次被从父母的身边被捋走,送到寄宿学校,当他们一出生,或者在四岁之前。
Joseph的父母,在他小的的时候,经常无缘无故地打他,折磨他,甚至用铁链子,酒瓶子砸他;很多时候,他非常不能理解,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。其实他的父母在经历寄宿学校的早期的创伤后,他们在以代际传递的方式,无意识地传递给了下一代。
Josph,面临着同样的命运,他小的时候父母不断地搬家,把他隐藏起来,这样才得以幸免没有被送进寄宿学校。但他经历的成长的创伤,一点也没有使他豁免于精神上的痛苦和无助,他同样陷入不可自拔地人生泥沼。
太艰难了,他用了20年的时间,通过心理咨询和自己的努力,对自己和家族的创伤进行艰难的修复和对社会的重新认同与回归。
虽然艰难,Joseph 还是在一片精神的废墟上站立起来。过程虽然漫长,但他无可选择。今天他成为一个印第安原住民血泪史的写作者和讲述者,去为他的社群争取应得的利益和尊重;同时与殖民者的后代,重新建立连情感和心理的连接,重新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讲,已经面目全非的世界;这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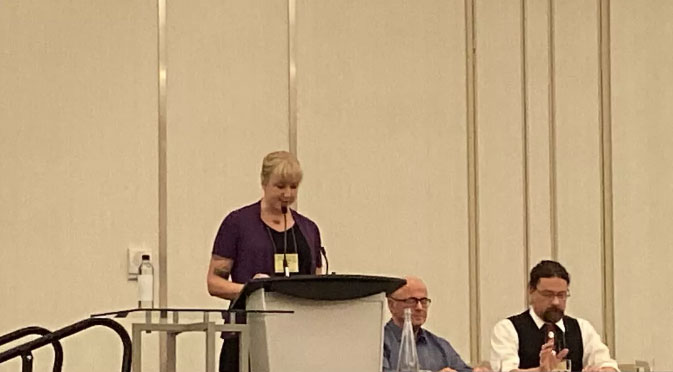
会场的气氛凝重,很多人的眼里充满了泪水,不少人沉重的呼吸。多数参会者是白人,有的是第一次了解这样悲惨历史。大家被深深地震撼,沉浸在巨大的悲伤和丧失的体验中。
有的学者发言,表达了自己悲伤的感受,以及觉得羞耻的体验。有的学者表示,其实不是Joseph有问题,而是白人殖民者有问题,今天Joseph的血泪故事,恰恰也在疗愈这些殖民者的后代。
寄宿学校,一直到1996年才在加拿大关闭了最后一所。
全体会议后,进入了小组讨论环节;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表达了相似或不同的观点和感受。

会场的气氛凝重,很多人的眼里充满了泪水,不少人沉重的呼吸。多数参会者是白人,有的是第一次了解这样悲惨历史。大家被深深地震撼,沉浸在巨大的悲伤和丧失的体验中。
有的学者发言,表达了自己悲伤的感受,以及觉得羞耻的体验。有的学者表示,其实不是Joseph有问题,而是白人殖民者有问题,今天Joseph的血泪故事,恰恰也在疗愈这些殖民者的后代。
寄宿学校,一直到1996年才在加拿大关闭了最后一所。
全体会议后,进入了小组讨论环节;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表达了相似或不同的观点和感受。

